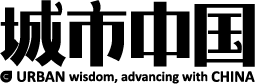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0期——“重庆直辖”
文/贾樟柯(北京)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三峡工程由来已久,从民国孙中山时期开始提议到1992年最终通过决议修建,它一直是中国人关注的焦点,甚至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国际性事件。它牵动了一百多万人口的移民,也牵动了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长江沿岸历史城市的拆迁,牵涉到那么多的文物和古迹,在人类历史上这都是空前的。但这个空前的事件在一开始对我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我出生在山西,又长期居住在北方,在中国南方修建一个水电站,感觉和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对这个事件本身的理解也是抽象的,正如所有的媒介报道,都从宏观层面对它进行读解。“100万的人口移民”在一个国家里、一段历史中都只不过是一组抽象数字的书写。如果我们只是通过数字和媒体报道而不是通过普通人真实的生活展开的叙述,就很难去体会到这个巨大的变革给个体所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所存在的个体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描述的,因为恰恰是这些数量巨大却被抽象概括的现实生命才离我们的生活最近。
【三峡】
在2005年我第一次去了三峡,亲眼看到了三峡沿岸城市的移民和拆迁。那次采风带给我的一个巨大改变就是摆脱了这些数字下的麻木。当我看到上万人聚集在鹅卵石河滩上等待移民出航的轮船,向亲人挥手告别的身影,握手、拥抱、哭泣、微笑……这些画面蕴藏的力量直接刺激了我的神经。在拆迁现场,用当地的领导的话来说就是“两千六百年的城市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拆掉了”,这句话里提示了一种速度,这个速度既是中国当下城市建设、更新和发展的速度,同时也意味着无数的普通人的生活在瞬间发生改变——我们——所有普通的人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中。这正是现代启蒙中的“民生”问题。在一个社会反差较大的国度,存在着多种现实,让另外一群人了解另外一种现实,记录和描述普通民众真实可感的记忆,构成了拍摄《三峡好人》这部电影的动力。
2006年的时候,画家刘小东开始策划以三峡库区移民和拆迁为背景创作一组组画《三峡温床》。电影《东》就是拍摄这件事情的记录片。《东》以画家创作作品为线索,拍摄记录了拆迁工人的生活。但是仅仅有纪录片是不够的。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被记录的人物角色在面对摄像机镜头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人际关系并不是那么的真实,它会有所回避或有所夸张,于是《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以故事片的方式同时进入拍摄。通过重新建立故事的叙述来把这些隐性的东西重新展现出来。这两部电影,一个纪录片和一个故事片,是通往叙述现实的两个方向。
【奉节】
在拍摄之前,剧组对三峡库区各个城市都进行了考察,而最终选择了在奉节县拍摄。一个原因是当时奉节县还剩一半以上的旧城未拆迁完,这是有利的电影主题环境同时也是整个三峡库区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奉节有着其特殊的文化表征。从古诗中“朝辞白帝彩云间”到现在第五套人民币10元纸币背后的蘷门关,整个文化、历史、自然地理甚至经济在这样一个江边小城都有所提及——这是电影值得展现的文本。在拆迁的废墟中,当人们在忙碌他们的生活时,这些文化可能被屏蔽在能够注视的范围之外,但是它们一直都在被使用。长江游轮上解说员对三峡风景的介绍以李白的古诗为开头,韩三明和工友们交换欣赏人民币背后的风景。影片中这些片断联接了宏观文化和微观生活的缝隙,将这一时刻的现实放置在了整个连续的历史中:当站在奉节看蘷门的时候会想到刘备一定也看过,李白一定也看过,我们跟古人还在分享同样的东西。
【烟、酒、茶、糖的电影】
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有一种传统,即只记忆那些宏大的事物、重要的时刻、庞大的数字,重大的事件。这种传统使得整个民族的历史从不描写最朴素的生活,也从来没有涉及到最微小的物品。
“烟”“酒”“茶”“糖”是剧组在三峡库区拍摄时常常见到的四样物品。常常见到并不表示这些东西的丰富,相反正是因为物质的匮乏使得这些物品成为当地人交往中重要的沟通。剧组到一个民工家里去采访拍摄时,屋子里面家徒四壁,四根板凳围着一个煤炉烤火,他用啤酒来招待我们,但每瓶三块钱的啤酒对他来说是生活的奢侈品。朋友一见面,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先递根烟,烟是男性之间打交道的重要方式。茶和糖也同样在沟通着人际关系,有人生病送糖,朋友之间送茶叶……对于缺乏物质的民众来说,烟酒茶糖比细腻的语言显得更有力量,也更能表达情感。
同时“烟”“酒”“茶”“糖”这四种东西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国家重点调控的物品,而三峡工程本身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有计划的修建、有计划的移民,有计划的拆迁。作为一个国家的宏观计划,烟酒茶糖从一方面对应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结构,也从另一方面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勾勒来自民间最朴实的感受。如果说三峡工程修建将百万移民的命运共同联系在了一起,那么“烟”“酒”“茶”“糖”则成为在这场漂浮命运变迁中联系所有人们感情的微小事物。它们成为《三峡好人》隐性章节的线索安排。
【飞来、飞去——神话、现实与未来】
生的被动移民,还有数量巨大的移民是自觉外出打工的移民。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外出打工不仅是解决个体经济问题的途径,也被当地人看作是体验和融入外界文化的主要方式。在对当地一家人采访时,女主人长久地注视着墙壁上的NOKIA海报,并骄傲地告诉我们她的女儿在这家公司上班。这个细节后来成为电影中常常出现的镜头。面对现实时的无所适从,使得他们将注视的目光放在未知的外界。长久的注视一张广告海报,或站在窗口向远处眺望,这种眺望和注视构成了他们对未来生活和远处生活的理解—— 一种符号性图景的描述。然而未来是未知的,对于那些在现实中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人们,未来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暗示和现实的同构,未知的漂浮的不能自我主宰的命运;另一方面暗示新的可能的希望,对未知的憧憬,仿佛应该有某种超越现实的神话在他们眺望或注视的远方。
三峡地区的文化中有很多神话故事。神女峰的眺望,巫山云雨的神话,天气变幻无常的种种奇幻的景象,这些故事从古流传至今。甚至当前的现实——在一年之内,百万人口将从这一地区消失不见——这一事件也带着超现实的色彩。这些故事赋予了这个地区很多神话的情绪,它们丰富了简单化的现实。
《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中,主演韩三明和赵涛站在山头眺望远处飞来又飞去的飞碟——巫山云雨中的奇幻事物;移民纪念碑神秘的飞走——“一夜不见”的百万人口,这些镜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三峡地区神话气质的现实表达。神话不仅是古代遗留的文化,同时它们在对应实实在在的现实时还指向了未来——那个无数普通的人们眺望远处的未来。
【电影之后】
《三峡好人》拍摄完成在上海放映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当时移民到崇明岛的移民来观看这部片子。在放映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当电影播放到人们等待移民的场景,画面出现一个人紧紧抱住一棵橙子树,要把这棵树连同这些泥土带到崇明岛去时,一名观众泪流满面。这名观众后来告诉我们他的经历跟电影里面那个人一模一样,也是怀抱了一颗树苗,而当他把这棵树带到崇明岛栽到自家院子里的时候,一年之后这棵树没有活,死去了。他说:“我们所有东西都可以搬运,但是我们的天气,气候,土壤,我们的风水都是搬不了的。”这些细节都是非常可感的,来自民生的反应。
以三峡建设为背景来看这部电影,它是中国当代快速发展的一种集中表现。面对这个题材的时候,去考察在这件大事背后每个人的生活,对他们的生活保持敬意,记录在这个发展和变迁过程里面所有人民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我想这就是我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