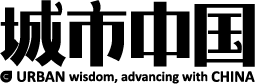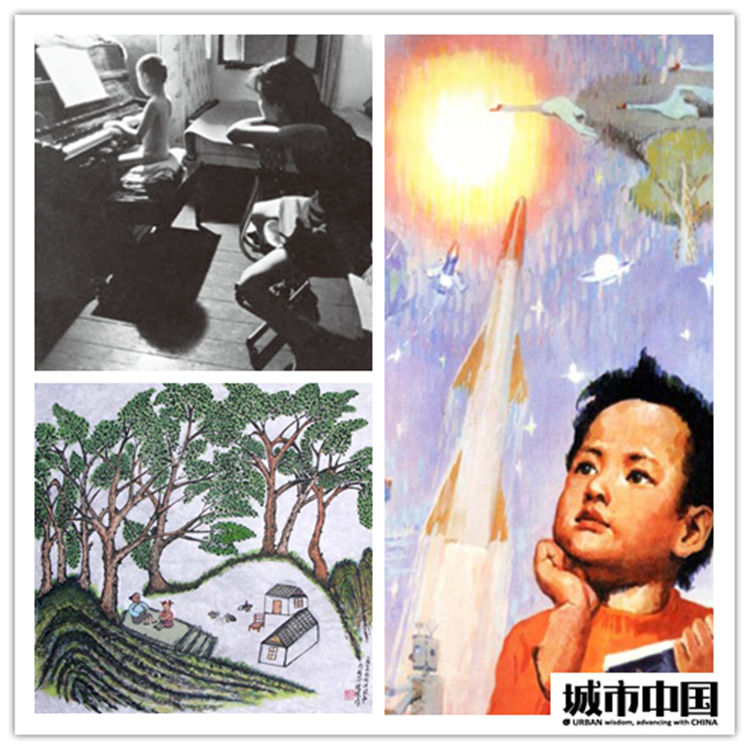文/潘天舒(上海)
萨拜因曾说“良好的出身、良好的教育、良好的社交关系、悠闲的生活等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和财富连在一起”,社会的分层在某种意义上说与人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文化资本成为一种势能,根植于家庭教育当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是人们对于文化优势的自然地追逐。
儒家理想中的家庭教育可以说是实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人生终极目标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如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目的简单地理解成将后代培养成能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所谓“外圣而内王”的经世之才,未免失之偏妥。其实在中国家庭教育过程中,穷九经三史诸子百家的内在动力并不只源于道德教化和塑造人格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以通过科举考试(中国传统社会中少有的平等竞争机制)的成功,来达到光宗耀祖即维系传统中国家族垂直一体化这一实实在在的考虑。
在近现代中国,家庭教育在实践中逐步成了一种对学校教育中所积累的文化资本的制度化的充实方式。在这里“文化资本”是指将来自良好家庭的文化优势通过教育传导给后代,从而维持不同阶级差异的过程。“文化资本”的这一社会学概念,将统治阶层拥有的经济力量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文化资质加以区分,从而使我们对传统和现代中国语境中家庭教育作为生产、控制和传承文化资本的必要手段,有更为明晰的认识和理解。在社会学家眼中,阶级差异不仅在经济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而且还在物质和文化消费领域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文化资本似乎带有某些“遗传”特征,如人们的对于琴棋书画的精通程度和古典音乐的品味,通常被视为家庭教育质量的一个衡量标准。
那种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积累文化资本所形成的“惯习”(Habitus),在不经意间成为自身生活实践的有机部分,甚至于变成一种身体语言。除了穿着打扮和举手投足之外,我们在各种场合说话时的遣词造句也在显示自身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种微妙的运用文化资本的方式。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国,这种文化资本表现为一种“贵族气”的口音,腔调和优雅的谈吐,能够显示说话人的教养和教育程度(即文化资本的拥有量)。同样,在九十年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居住在上海棚户区苏北移民的后代,都以学会说一口带有宁波口音的沪语,来显示自己拥有与上海人(浙北和苏南后代)同样文化资本和社会地位。
我们在中文语境中常常使用的“没有文化”或者“没有家教”的说法,用社会家的话来说,无非就是由于阶级出身而导致的“文化资本”匮乏。作为古代中国家教经典而传颂的“孟母三迁”,其实完全可以被视作父母竭尽全力为后代获取文化资本而创造最佳就学环境的社会学来解读。据本人观察,在北美,来自大中华地区的华裔移民之中,就有不少类似“孟母三迁”的逸事。为了使在美国出生的下一代免受其苦,这些华裔们自己含辛茹苦,生活简朴,而在添置房产时特别注意选择上好学区。所谓好学区其实就是房价居高不下的中上收入阶层的居住区(上海人所说的“上只角”)。
在当今中国类似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家长们为了家庭教育之所以付出昂贵的经济代价,不仅是由于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价值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是在为后代争夺文化资本的一种奋斗手段。然而经济资本的多寡往往限制了其积累文化资本的能力。因而将家庭教育作为积累文化资本的“风险投资”,与延续父辈理想、洗刷劣根性、家庭暴力、代沟之间,必然会存在一种矛盾的关系。而强制性的文化基因输入,必然使家庭教育的模式更趋单调呆板(如由钢琴课、英语课、电脑课等组成的“家教”产业化菜单),与兴趣引导和因材施教等为古今中外有识士共同推崇的家教理念南辕北辙。
当我们以一种马克思式的目光来审视家庭教育与所谓“文化资本”的积累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意见。我们不难发现, 在当代中国,文化也被分成不同等级,与社会分层相互适应。那些担当精英文化代言人的文化大师们(恕不点名),通过媒体引经数典,对“文化遗产”发表高谈阔论。在表面上看,是在显示自身家教和学养的丰富, 而实质上不过是在将自己的文化资本不断转化为经济资本。另一方面,为弥补缺少“家教”、文凭或学术职称的不足,国内一些企业老总购买网上文凭、通过捐资担任知名大学的名誉博士,又何尝不是一种将经济资本转化成为文化资本的捷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