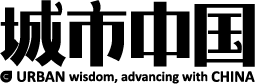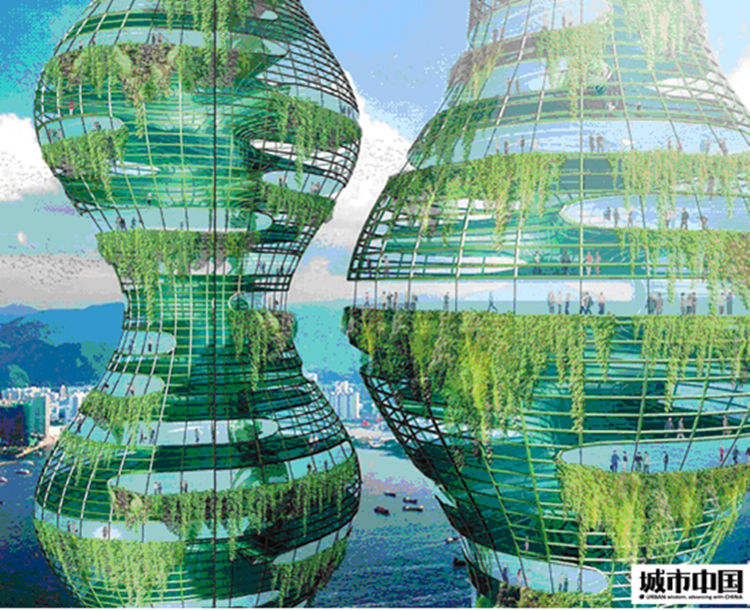文 / Harry den Hartog
翻译 / 袁菁
城市若想常青,绿地就绝不可少。但是中国高速的城市化扩张,导致了目前城市化发展中遍存着绿地数量与质量与需求的不对等现状。这一问题也普适于全球各城市的绿地发展。是时候让绿地为城市发展的“欢乐欠奉”负些责任了。在全球困于绿地之惑时,彼此互享绿地经验,或许能让城市在绿意中再度开颜。
作为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空间创造才能。公园空间在他们的手中富于了多样性的功用:融放风筝、打太极,闲坐长凳、草坪,游戏,聊天于一炉。在中国特有的语境中,公园生活极具社会性内涵。我们不妨来参看一下鲁迅公园这个优秀范例。热情高涨的民众会参与园内的各种活动。此外人们乐于在园内聚首见面。最具蛊惑力的一幕出现在园内民众自发为音乐造势并流连于此的景象。有人摆弄着自带的乐器;也有自行组建乐队,让人民大众在户外爵士曲中翩然起舞。
目前众多新建的商业中心同样也有绿地的身影。即使“绿洲”的公共利用问题仍然莫衷一是,无从定论,但它们的存在还是为“水泥森林”的城市视效扳回一城。
西欧众多的城市公园反而不及中国公园,具有如此之高的使用率和人口密集度。各种文化活动一般只选择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公园内举办。在我的故乡鹿特丹,大公园常被作晴日户外野餐与烧烤场地之用。地中海人特别喜欢公园的户外活动,常是边准备餐点,边席地享受温煦日光。
一年几次的大型剧团演出、音乐会在公园上演。除却大型活动外,公园可用于读书、打盹,全因个人喜好自便。孩子们常来公园踢球,打乒乓。不过每年4月30日是个例外。该日,荷兰许多公园的开放只为女王庆生之用(女王节)。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Vondel公园,成为开放性的集市,且吸引当地居民来此自发组织活动。孩子们制作着手工艺品,将他们售予路人。园内会开展诸如互掷注水气球的游戏,当然也有颁发小奖品的竞赛举行。女王节当日,市民们在自家居所前的街径上设摊,兜售着自家的旧书籍和老家具。整个城市流动着街边互售的气氛,往往演变为全城义卖。
不过自从荷兰几乎家家户户有了花园开始,这种情形就有所变化。大部分城市公园逐渐人丁荒疏。
当然,还是有市民们愿意牵着宠物狗来草坪上欢跑一阵,或者踢场足球。但相比中国公园,大部分荷兰公园仍显得落寂、空阔。正因如此,沉静、整饬的公园氛围内更易寻得安谧、沉思的空间。
城市与乡村:唇齿相依的“二重奏”美国不少大都市,譬如纽约、芝加哥、华盛顿皆凭借其出色的绿色建筑、林荫大道、地方公园而蜚声扬名。可但凡虑及美国国内仍存在着的公共公园、花园匮乏问题,建设原始化景观的梦想一下子就远如海角天涯。
William Cronon曾在其饱受称誉的“自然都市:芝加哥和大西部”(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and the Great West,1991)一书中写到城市与乡村的那种唇齿相依的“二重奏”关系:“自认能在山乡绿湖或橘色云朵中择其一的想法,不啻是自欺欺人。他们皆为风景,城乡都是我们的责职所在。”Cronon在书中描述着城市与乡村的共生关系。
作者已然意识到,广袤腹地在城市发展中所承当的基建角色。这种理论同样适用于城市和乡村间的关系:两者并非简单对立,而是共生共济的平等个体。假如没有广袤的腹地,芝加哥就不可能跃升为如此重要的国际大都会;反之,腹地缺少芝加哥所提供的以买卖、配给为基础的消费品交易,自然也无法得以繁荣发展。互为表里的城乡关系本是一条荣损相扣的发展链。
城乡的密切关系在市场层面就可见一斑。谷物、肉类和木材是芝加哥贸易市场的重要支柱。然而市场内部充满着荒谬吊诡以及不和谐因素,影响着这三大支柱产业。随着市场重要性的与日俱增,市场流通与贸易源头的沟壑也在不断扩大。
Cronon书中所描述到,一个世纪之后的今人早已对“能致动物于死地的遥远距离”这类概念十分隔膜。伴随农业、工业革命而生的科技、金融架构之下,标准化的谷物、木材和肉类贸易高速流通。但也正是在这一演进中,食物生产失去了曾经的透明度:生产、加工、分配、消费的工序环节彼此分离,毫无瓜葛可言。西部超级市场中贩售的肉类,常常裹在塑料袋里,有时甚至在屠宰许多周后才得以出售。肉类被冷冻,也常被注射添加剂。塑料袋的包装过程,离间了动植物在起源上的关系。
就像芝加哥这类城市,虽然已成为全球经济系统的一部分,但却在自己的物理尺幅内丧失了与内陆(大西部)的密切关联。
【重拾城市】
据Cronon所言,“第一自然”满足着人类不加餍足的消耗需求。而现在,愈来愈多的城市居民也投身于植绿行动以夺回城市“失地”,这种行动正复苏、续接着城市与乡村间业已断裂的纽带。
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市的当地管理基层组织重申了土地应征用于建造社区花园。在此背景之下,大部分的城市地方议会默许城市居民的自发植绿行为,并报以鼓励态度。
二战后迅速崛起的美国催生了一批暴富人群:他们配有了私人小轿车,驾离了穷乡僻壤,也抛下那些日益凋敝的旧区,以及生活其中的衰败人群。1960年代末期爆发的那场种族骚乱,终于成为了该地区居民奋起改善居住环境的转捩点。1973年的纽约下东区,本地居民LizChristy创立了“绿色突击队”:这个非营利性组织意在鼓励邻里发出“废置土地用作社区花园建设”的宣传倡议。
这片曾栖息着流浪狗、瘾君子的地块,终于被当地志愿者们洒扫至焕然一新。“绿色突击队”散发的小册子内,则讲授着如何将充有种子、水、化肥的气球或圣诞装饰物的“种子手榴”,用抛掷的方式丢入无法涉足的地域。
“种子手榴”会在底土和一定尺幅的地基上生根发芽。但要先领会一些抛掷的诀窍:高抛“气球”,低手抛掷“圣诞饰品”。归功“种子手榴”的“翻墙越岭”,城市围墙中野花恣肆怒放。
Liz在身后被推奉为花园之母,Liz Christy花园则成为了一种纪念。这座由有机薄质表土围合而成的社区花园就坐落于休斯顿大街地铁站边。它是高冠曼哈顿之最的水杉树家园。内有一池鱼塘,有位养蜂人在里头工作。第一批小型花园的成功运作带出了好头:美国迅速掀起了花园建设的风潮。
土地的真正持有者——纽约住房和养护部门容囿着这些花园的存在和蔓延。除了象征性收取每年一美元的养护费用外,绿地的使用者还要听询每月发布的相关使用公告。那些价值稍逊一筹的地块则可以签订5至10年的租约。花园可按使用者的意愿绘制设计草图,以便成为日后邻里餐膳、孩童聚会、讨论研究的公共空间。自然,其样式也是从平淡无奇到颇具独创不等。
除了蔬果园地的花园设计外,广场方案的设计草图中,会规划有民间艺术的嘉奖台、体育场,甚或花卉环抱的911纪念坛。公共花园的利用通常颇为审慎。不过,更多的公共地块被定位为果蔬园。可花园持有者为避免损坏等诸多不便,常在花园周边添设围栏、篱笆。想来游园的民众却因并不常驻此地的志愿看守者而吃够“闭门羹”的苦头。
监管、养护,以及为花园筹集款项的职责落在了当地居民的头上。许多树木、作物、种子和肥料就这样,以“以货代款”的捐赠方式送达到了居民的手中。值得一提的是,Liz Christy花园的水塘边还有个关乎“慷慨”的布告,提醒人们不要在池塘投生、放养鱼类或乌龟。
在贫瘠地块上,人们往往通过种植庄稼作物以糊口谋生。这类情况普遍存在于芝加哥,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果蔬园因而成为花园建设的可操作途径之一种。
也有迪士尼这类商业裁团,为招徕公众注意,博取名声,在下东区大规模地投钱建造花园。1994年,新当选的Rudolph Giuliani曾决议在纽约大规模兴建花园,但后来却推诿城市发展亟需筹措资金之名,转而大量兴建居住住房。
是时,当地的居民再次投身夺回“绿色失地”的活动。他们以现有法律为依据,并且成功上诉:住宅区域内,每千名住户最低需配置2.5英亩尺幅的公共花园。得益于他们卓有成效的努力,当前该城已享有超过850座社区花园。
可移动的城市农场(Mobile City Farm)是基于社区公园概念的一次趣味转型,也是芝加哥资源中心的自发性非盈利组织(ResourceCenter Chicago)。这类种植果蔬的农场,常择址于尚未发展定型的地块。这种颇具反荒圮、反个人独占取向的公共花园模式,不仅能阻止土地因失管而流于荒芜,同时也增强了土地财富价值的风险抵御力。
这些美好的果蔬花园,给陷于绝境的失业者以园艺学习的机会。邻里集群间因蔬果共享而构建出良好的人际关系,熏陶出慷慨慈爱的风俗。此外,培育出的大量农作物可以在市场中销售;芝加哥的一些顶级餐厅也会成为他们的常客。
关于自发、谨慎的探索土地利用之风气被秉承至今。更可喜的是,这种良好的风气在美国郊区不断蔓延扩展。建筑师Fritz Haeg在几年前实施了一个叫做“可食用庄园”的项目(’Edible Estates’)。在他的经管下,美国郊区特有的典型有序的草坪被“改制”为种植可食蔬果的花园。
在“可食用庄园”中,郊区居住者有机会亲身感触季节更替和有机种植的乐趣。不过此前,他对居民的系列调研结果则颇令人震惊。这些郊区居住者不愿种植花卉、蔬菜,而中意更具保值性的大面积草坪的前三位理由是:害怕土地财富值的下降,害怕虫害,害怕邻居会偷窃瓜果。如此看来,“可食用庄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毕竟,这个自发活动已结出了蔬果花园之实,也培植出了牧场草稞这类土生土长的作物。
此外,坐落在城市远郊的社区支持型农场(Communi ty Suppor ted Agr icul tureFarm)乃是城市花园的“辅助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百多家社区支持型农场纷纷起建于美国都会的周边区域。这个席卷北美,超过10,0000家庭参与的活动,共谋着乡村互尊互助的社会经济学范型。在此范型中,公民不仅管养农场,也流通互换食物。
这股社区支持型农业运动(Commu n i t y Supported Agriculture movement)之风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农人、公民、科学家共同联手创办了日本有机农业协会(Japanese OrganicAgriculture Association)。创建该协,部分得因于对农业种植过程中化学药物滥用的不满。另一方面,协会也意图探寻、解决城郊居住区域的扩容之策——《城市字典》(Urban Dictionary)诗意地将这此形容为“大道,是曾于此处倒下的树种之墓志铭”(”where the people who cut down treesand name streets after them….”)
不过协会更主要的意图是创建具有多样选择性的食物配给系统。在这个谓之“Teikei”的系统(可直译为:将农夫头像印制在产品或包装上)中,生产者、消费者构成伙伴关系。同时它也为农场自产作物与其流通置换产品搭建渠道和平台。在这种平台模式之上,农人确保有足够的收入,并对自己土地投入再生产,而民众则确保享用到新鲜蔬果,以及农场庄园所带来的清新户外环境。运作良好的协会,关注着食物链的透明性、质量、口味、食品安全性,也保护了小规模的农场的营运和绩效。
它已集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于一体:这类小规模农场,在社区区域中形成了配给网络,供给近距住户以各类花色品种的食物,免除了人们对基因变异、添加剂的担忧。与此同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得到控制。
在当地农场的良好收成之下,市场供给给附近村镇的果蔬产品绰绰有余。农人亦可自行去集市销售果实——对我们而言则有机会熟识那些为我们提供食物的人。这一良好的运作体系,重新续接了生产、分配、消费和循环之链。
除了公民们的自发植绿行为,有关鼓励花园建设的政策也在不断地被制定和推行中。无论公民和政府,都意在共建更绿的城市前景。目前,芝加哥的当地政府正积极地在当地居民中推行屋顶花园的策略。其中,最富象征性的市政厅屋顶花园建设,已在筹措和施行中。屋顶蔬果与地面景观,以及大面积铺设的本地牧草植株,共同为城市的巨构系统增添了绿色的肌理。目前,在芝加哥,由绿色屋顶连缀而成的地域已达100公顷之多。新千禧公园部分建筑顶上,编上号的小院内种植着蔬菜,遥遥比对着地面原始无垠的草原景观——这些原始植株是“已经消失的第一自然”的挽歌与“塑像”。
在中国的城市同样不缺此种案例,比如成都的屋顶花园建设。屋顶花园的理想化策略为城市高密区域提供了某种解决案例,也为接续“第一自然”时期的景观风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对于高速增长中的城市住宅来说,屋顶花园不啻是对拥挤稠密的城市建筑的一次“垂直逃离”,基于此道,公民大众再度寻获了洁净蓝天和新鲜空气。
不过,垂直公园的建造理念多少已经过时。新近夺得南韩首尔附近Gwanggyo Power中心的荷兰MVRDV建筑师们的竞赛方案,就与上述的垂直花园理念相仿。这个方案由一系列草木繁茂且状似岗峦的多主题建筑群所组成,意在冲击城市更高密度的标杆,而覆盖的山林状景观即是建筑群的屋顶立面。
作为社会和文化事件的绿化当下,公民和政府正在施行的绿化举措即为Cronon书中所言的“第二自然中的社会构成”(”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secondnature”)。城市和自然看似矛盾对立之处,就是彼此的胶合之点——城乡已密不可分。
同样地,对食品安全以及与“第一自然”重新建立新型关系的渴求也在不断增强。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贩售新鲜物品的商店和农场型市场已获得了公民的好评和首肯。连总统奥巴马都在白宫前的自家花园内开种农产品。
这股劲头也波及到了欧亚的诸多城市,城市农业和园艺浪潮悄然兴盛。在荷兰本土,对时鲜本土产品的供求量正在扩大,专职培训农人以及耕育土地的实验性活动也在展开。多方的共同努力,让荷兰的城市绿化已有小成:从农场型市场、街道农夫,再到社区花园。随着农业景观向视觉型消费的转型,公民社会和商业体系通过建立区域型景观基金,成为了保育文化景观,重缀城市乡村纽带的共同推手。
绿化、花园的营建,带有着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双重色彩。而这条绿化产业价值链,关乎人与自然关系模式的重整,也为人际关系的融洽拂来清风。毫无疑问的是,社区花园将会成为“教堂”、“酒吧”的双关语词,既供人以心灵自省,也让人眼观大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