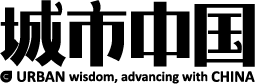文/陆铭 摄影/徐争 编辑/王文静
【人口,户口,城市发展不可承受之重】
当前,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改革非常紧迫。城市化进程没有充分发挥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
用。这些现象在本质上都与中国的户籍和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民进城工作和生活有关。关于户籍制度如何改革,现在的主导意见是,要“从中小城镇开始”。在成都和重庆两地试行的地票交易在本质上就是“土地与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但其推行范围却仅限于本市市域范围之内。
只有当政策允许跨省(市、区)的农业用地“占补平衡”,即在不同地区之间推进城乡建设
用地的增减挂钩,才能解决农民工异地进城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城市“要考虑承载
力”。但是,如果大城市承载力不足的话,那么多农民工不是已经在城市里呆下去了吗?以上海为例,2010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2220.83万人,户籍人口1412.32万人;来沪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829.82万人,占常住总人口比重为37.37%。从实证研究的结论来看,中国的城市不是太大了,也不是集聚度太高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要去限制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还是通过土地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来顺应企业和劳动力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集聚趋势?无论是理论还是研究的结果都告诉我们,应该选择后者。
那么,是东部城市的承载力高还是内地城市的承载力高?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认为东部的大城市有拥挤或者污染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把这些人放到内地,会发现生存条件远比东部恶劣,自然灾害也更为频繁,承载力实际上更差。所以,所谓的“承载力”其实就是个托辞,本质上就是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不愿意被外来人口分享。在中国,公共服务的筹资体制是基于地方财政的,所以地方政府提供的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平等地提供给外地人,本地政府和居民不可避免的心怀芥蒂。相比之下,欧盟规定只要是欧盟成员国的国民,就享有欧盟范围内的自由移民,自由经商,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无歧视的公共服务等一系列的平等权利。
那么,如果不能“从中小城镇开始”,小城镇应该如何发展?媒体和政府官员都说,中西部城市化、工业化道路再也不能重复东部城市“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可是,如果是一个地理等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要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还要接受上级的考核,如何招商引资?最可能招到的就是污染企业。我在安徽西部某市看到了据说是全国离市中心最近的中石化的工厂,我们开车到农村去调研,从市中心出发一会儿就到了,好象还没出市区呢。我就问当地的朋友,你们这样不影响城市的发展么?他说,影响啊,我们政府跟他们商量过搬迁的事,中石化说你要让我搬迁,我就走了。所以,在人没有充分流动起来的情况下,欠发达地区要解决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要顾中西部的环境,是难上加难。
而“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的方案,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相分离,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使得土地使用权成为可以跨空间再配置的资产。其价值体现在将城市近郊的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实现城市土地的增值收益。有利于提高农民,特别是偏远地区农民的资产收入,与中央扩大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精神一致。农民在进城后,其承包的农业用地则可以有偿地转让给农村集体,或以转包、入股等形式分享未来农业经营收益。今天,很多规划都是要把大城市限制住,人为去发展小城镇,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城市和小城镇都发展不好。
【民工荒,技工荒,一线城市的用工尴尬】
如果要缩小地区间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缩小人均意义上的差距。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特别是低技能低收入的劳动力流动,更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的差别,相反,如果限制住低技能低收入劳动力的流动,地区间差别反而会因此而扩大。
最近“民工荒”问题很热,很多人都说今天中国出现“民工荒”代表劳动力的短缺,有经济
学家称之为“刘易斯拐点”。可是,今天的“民工荒”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刘易斯拐
点”?中国今天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90%,而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8%,也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48%,而这其中已经包括了在城市但是没有当地户籍的外来劳动力了,只要他每年在城市生活超过半年,成为常住人口。如果出现“刘易斯拐点”,那么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就应该缩小了,因为城乡间劳动力自由流动,城市里劳动供给越来越多,而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出,其农业边际产量提高了,城乡间收入差距是趋于缩小的。虽然统计上2010年城乡收入差距终于有所缩小,但这才刚刚显现,而且是否主要是由政策补贴造成的,还需要研究。所以,今天中国出现的还不是一个刘易斯意义上的“拐点”。如果有拐点的话,我宁愿把它称作是一个制度的拐点。今年春节以后,“民工荒”再度显现,让我们大胆假想一下,如果把户籍制度全部废除了,“民工荒”还存在不存在?
我有一位在重庆某县政府工作的朋友,调研了60多户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户,但现在都待在重庆不出去打工了,他们说,“在城市里能干的工作待遇太低,好点的工作需要技能,我们又没有这个技能。”在扭曲的地价和工资形成机制之下,这个问题被加剧了。沿海地区的地价和工资越上涨,企业的反应是要产业升级,劳动力需求就越往高端走,但是现在农村里的大量劳动力存量是低技能的,于是,在被扭曲的价格下所出现的产业升级趋势,和现在劳动力供给结构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结果导致这一轮的“民工荒”是“技工荒”,产业越往上升级,技工当然越荒。很多人会说,普工也荒啊。如果在沿海的产业结构升级限制了普工的需求,那么,就会限制普工的待遇改进,再加上最近几年农业的比较收益有所提高,内地近两年来又在大量建设基础设施,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就减少了。可是,等高速公路建完了呢?
等农业比较收益提高的政策效应释放完了呢?等这些短期的因素都过去了,农民工还是要找工作的,那时,极有可能出现的一个状况是,他们已经难以在沿海地区找到与他们的技能水平相适应的工作。
【身份,身价,新生代农民工的一声叹息】
我们需要的城市化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面积扩张,而是要让进城的农民有就业,有保障,有足够的补偿,有体面的生活。以加快推进大城市降低落户门槛为导向的改革应有所突破,而户籍和土地制度的联动改革正是推进城市化,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国今天如果改革户籍制度的话,重点不应该放在中小城市,而应该是大城市。由于大城市更有利于提高收入和找到工作,自然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首选。但是,户籍却成为这些“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的尴尬。在中国,户籍影响着劳动者的待遇,拿中国的户籍和欧洲国家的护照相比,则意味着更多的身份歧视。
人口规模有利于提高收入水平,因为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来自整个城市,而低技能劳动者则与高技能者是互补的。不同技能的劳动力之间的差异还体现在各种社会福利上。在社会保障方面,全国未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外来劳动力如果缴费未满15年,那么当他离开原来工作的城市,原先单位为其缴纳的社保是带不走的。在公共服务方面,体现在教育上的差异非常大。基础教育(包括幼儿园)是按片入学的,按片入学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买房外地人在城市如果没有当地户籍,他买房子的可能性肯定要降低,因为自己未来难以长期留在城市。同时,没有户籍,孩子在入校时就会体验到待遇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因为中国的大学,包括部属院校,都是由地方政府出资,或是中央和地方共建。所以,大学在招生的时候,都给予本地生源更多的名额。
中国的一句古话叫“人往高处走”。美国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受高等教育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在不断提高的。但看每一个城市,只有大城市受高等教育以上的人口比重在不断提高。所以在经济学里面有一句话,叫“人才是往人才多的地方走的”,这就是因为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
这些与户籍联系在一起的福利差别远远比欧盟国家之间与护照联系的福利差别要大。在欧盟内部,一个国家的公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居住或者生活,这些在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别是没有的。更有意思的是政治权利,如果你是个德国公民,但在法国居住,你可以参加居住所在地的市政府的选举。因此,在中国,所有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差别共同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阻碍中国劳动力的地区间和城乡间的自由流动。
【品质,安置,不要“鬼城”要“魔都”】
鄂尔多斯——中国的一个城市“暴富户”,“暴富”主要不是因为羊毛而是煤矿,很多人家后院里就能挖出煤。富了就可以造房子,鄂尔多斯的新城康巴什因房产空置度高而被称为“鬼城”。
后来人们发现,鄂尔多斯人都到北京买房子了。可是,按照目前的逻辑,北京那么拥挤,房价那么高,应该在鄂尔多斯呆着啊!为什么不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北京的生活好,好生活跟服务的规模经济有关系,这就是经济规律。
今天,中国处在“经济分权”的体制下,每个地方官员的晋升就跟当地经济发展有关系,而且经济发展是按照总量而非人均来度量。所以每个地方都要想把自己规模做大,都希望留住本地的高技能劳动者,纵然要素的自由流动可能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所以产生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潜在的公共利益。但是,要素的跨地区再配置受到限制,这对今天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制约。
比照国际经验,我们不妨做几点大胆的预测。未来中国50%的人口将会集中到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这三大地区,即在中国人口峰值为16亿的条件下,有8亿人口集中于这三大地区。而从平均意义上看,就是每个都市圈大约居住2-3亿人口。如果每个都市圈10%的人口将生活在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那么,这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的人口规模估计要有2000-3000万左右。如果没有核心大城市的带动,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那些知识密集型的、对信息交流与创意要求比较高的行业,如金融、资讯、现代教育、设计以及文化产业等,都将缺乏竞争力,中小城镇的发展也缺乏带动力。所以,让人动起来,要让中国的居民特别是农村劳动力按照他们的自由意愿来选择到哪里去工作和追求更好的生活。(本文兼有教育部“非农业用地使用权跨地区再配置与区域协调发展”课题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