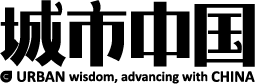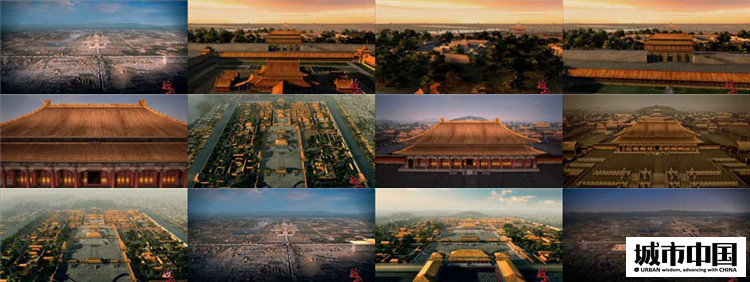2012年8月号《中国梦:重塑文化认同》已经上市,欢迎读者朋友们在各地书店购买,或在本刊淘宝店选购。
欢迎下载试读缩编本(PDF格式):本地下载
本期编按
“中国梦”:文化变法与国家认同
Chinese Dream:Cultural Reformand National Identity
文/匡晓明[本刊总编辑]+张宜轩[本期课题主持]
国家主义时刻的文化运动
Cultural Movement in Various Nationalistic Moments
201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发布了《中央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2年,中央宣传部门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汇编成书,出版了《论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摘编》。与此同时,2012年5月23日,适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中共高层进行高调庆祝。
文化是软的,像是活水,它可以滴灌艺术仙境的枝繁叶茂,可以孕育和折射社会生态的多样复杂,还可以堙没政治下水道的丑恶肮脏。但在国家主义的行动中,“文化”一词也容易从“软”变“硬”—这也是为什么在人们的脑海中,在过去一百年里,由国家所推动的文化建设的历史印象其实并不鲜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既往百年间,文化,曾是中国各个阶段运动和革命的主角。
文化是辛亥革命中,列位先行者所提倡的“中体西用”,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上宣传和践行如何移植西洋的科技和制度;它是鲁迅笔下改造国民性的呐喊,是“新文化运动”干将们颠覆封建残余,打破传统桎梏,大力推崇西学,创造新文化的风气。它也是共产党人借着“十月革命”的东风,在烛光下在窑洞里,从马克思的玄思中下降而至黄土,在解放区开创新风气和规制新社会的宣传工具和斗争路线。它也是“百花争鸣、百花齐放”时代的“阳谋”体验,是“文化大革命”的人间悲剧,几乎可以以此为界,中华传统和普世的人性价值纷纷断裂。直到八十年代,中国人又一次在文化的土地上站起来,悲欣交集地探讨着何为美丑,何为自由的基本命题,也不可避免地触及“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冲突。文化这个大缸不断地被打破、重造,再打破,里面装着各种混合液体—酝酿中国人传统根性的酵母,酝酿西方和现代性的酵母,不断地在发酵。
因此,本期首先要完成一个有趣的历史回顾:针对过去一百年中三个文化活跃时期的“文化梦”,即“新文化运动“时期,延安解放区时期,以及八十年代文化热进行梳理和总结。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视野中,我们试图并置这三个历史时段,发见三个文化梦之遗产,以此观照当下的文化语境对它们的各自因袭。
“软实力”:从合法性到认同
“Soft Power”: From Legitimacy to Identity
当下的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跑道上一路狂奔,“体用”之争、“左右”之争、“社资”之争、传统与现代之争,都在“不争论”的发展中被悬置。然而,一个大国的文化生态现状是异常复杂的,相较之下国家对文化的解释力却是薄弱的—虽然偶尔也有惊人的行动力。社会快速发展和严重的阶层分化催生道德滑坡和认同感缺失,市场的发育和民间力量的壮大,让以往的管制手段日显难为。同时,中共所沿袭的话语体系也在危机和对外交往中屡屡受挫。这就是当下中国内外交困的政治和文化现实。
因此,中共中央在“西强我弱”的基本判断下,进行“文化强国”的号召,其中暗含着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脱节的期望;提升“软实力”被看作是缓解国内社会危机的工具和平衡市场因素的砝码。“软实力”的推出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大力宣传的提高人口“素质”的做法如出一辙。一经提出,它们便成为贯穿一切领导讲话、政策文件、民间实践指导的关键词,最终变成政治上超越左右,既凌驾于体制机器之上,又渗入组织毛细血管的,从各个层面进行社会动员的超合法性力量。
“软实力”从提出的那一天起,便成为塑造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通用工具。而它恰恰也命中了当下中国的重要问题,即如何在重塑文化自信与融入世界文明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西方人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未来的东、西方,不管是从“和谐拯救危机”达至“世界大同”,或是在“文明冲突”的框架之上鼓吹“中国威胁论”,这不仅关涉到全球视野中的“中华文化”自身的活力与给养,也关系到中国人对“中国”这个在传统和现代中翻滚形成的概念的重识和认同。这是一个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内消化的双向过程。在本期开篇对历史学家葛兆光的采访中,通过追问“何为中国?”这个问题,他将逐步澄清中国认同问题的复杂性来源,同时也透过多面而复杂的国族认同问题,将我们的视野引向一条达至理性民族观的道路。
针对这个问题的文化面向,本期杂志将从“中国”这个意涵丰富的观念出发,透视认同问题的复杂性。首先,李晓东教授在“中国式空间观”的命题下,阐释了中国古代发展起来的视觉空间观念在艺术与建筑学方面的应用;这是一个与西方殊为不同的观念体系,可以透过空间见到更强烈的中国认同。中国式的教化观则透过孔子学院近期的海外实践反映出来—从树立合法性到激发认同感,路途毕竟艰难。而德国人卢安克在中国乡村的教育实践则是一记反题:外国人来解决中国问题,是否会不为文化因素所限而更直接有效?
“中国梦”:认同镜像与文化变法
“Chinese Dream”: Mirror Image of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form
对应于理念上的“中国”,我们不妨来反观中国现实:中国人通过各种方式移民到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波波的“移民热”伴随海归的脚步,实现了一个中国与世界双向认识的过程。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可以实现“美国梦”了,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否有一个“中国梦”呢?“美国梦”的历史叙事包含了一个很长的时段,最终在二十世纪末达到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之处,这个梦也是其在近代形成全球霸权的个体缩影。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的梦都被比下去了,甚至幻灭了。如果“中国梦”曾经被造/做过,那么究竟有多少这样的梦,最后又是怎样幻灭的呢?从袁世凯的“皇帝梦”,到共产主义理想中的“集体梦”,再到改革开放的“个体梦”,不同的梦境反映出社会文化情景的更替,也在这一次次“发梦”中,中华帝国时期与近代变革时期联系起来了,中国传统的静态社会观与西方的动态发展观对立起来了。
提出“中国梦“这个词,本身就要求我们在镜像中观看中国的认同困境—不停地从历史中、从西方看到当下中国的镜像。中华的影子里,有各种西方的镜像,有各种传统中国的镜像,也有经多次反射甚至折射后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混杂的民族和个人镜像。循着这个过程向未来探看,我们继续塑造中华认同的路上是否会重复出现或生发新的文化困境和诱惑呢?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在宏大理论和个体叙事中锚定并再造文化认同的因素?
在本期杂志的第二部分,我们采访了多位文化实践者,他们或是艺术实践的守护者,或是执着于发现和保留民间传统文化的媒体人或出版人,或是上世纪60年代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的故事是特定文化语境和时代条件的产物,但透过他们的讲述依然可以管窥“精英”实践力量介入民间中国的情况,重新思考知识精英保卫社会,保卫文化的努力。在最后,通过对“中产阶级”和“归国留学生”两个群体的命运追溯,我们试图反思“美国梦”之中国化的历史现实,也以此开启“中国梦”的世界性想象。
本期目录
中国梦:重塑文化认同Chinese Dream: Remodeling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目录 CONTENTS
6 刊首语 EDITORIAL
一项政策的遗产:论计划生育制度的现状
The Heritage of a Policy: Reflecting on One-Child policy
匡晓明[城市中国总编] KUANG Xiaoming[Chief Editor of Urban China]
10城市报告 CITY BRIEFING
18 城市研究 URBAN STUDIES
巴黎环城铁路的前世今生
History and Status Quo of Chemin de fer de Petite Ceinture
陆超(南京) LU Chao(Nanjing)
24 房产智道 REAL ESTATE REVIEW
资源型城市的矿藏Mineral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刘懿[城道顾问] LIU Yi [Chengdao Rroperties Consultancy]
26 编按 PROLOGUE
“中国梦”:文化变法与国家认同
Chinese Dream: Cultural Reform and National Identity
匡晓明[城市中国总编]+张宜轩[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KUANG Xiaoming[Chief Editor of Urban China]+ ZHANG Yixuan[UCRC]
28 图解 INFOGRAPHICS
一个世纪的“中国梦” Chinese Dream in a Century Time
张宜轩[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ZHANG Yixuan[UCRC]
30 问题是:何为“中国”?
访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
The Problem is: What is Chineseness?
Interview with GE Zhaoguang, Dean of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葛兆光(上海) GE Zhaoguang(Shanghai)
36图解 INFOGRAPHICS
同源异流:今天的汉字文化圈
Tributaries from the Same Source: Nowadays Sinosphere
任菲菲+张宜轩+刘懿[城市中国研究中心]+袁菁[城市中国] Fairy[UCRC]+ZHANG Yixuan[UCRC]+LIU Yi[UCRC]+YUAN Jing[Urban China]
38 图解 INFOGRAPHICS
百年文化梦
Three Culture Dreams in a Century Time
张宜轩[城市中国研究中心]+袁菁[城市中国]+李丹[城市中国] ZHANG Yixuan[UCRC] +YUAN Jing[Urban China]+LI Dan[Urban China]
44 孔子学院的民间模式
访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周晓霞
The folk mod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Interview with Zhou Xiaoxi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a East Normal University
周晓霞(上海) ZHOU Xiaoxia(Shanghai)
48 如何和留守儿童一起创作
How We Create with Stay-at-home Children
卢安克(长沙+板烈) LU Anke(Changsha+Banlie)
52 中国式空间观
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晓东
A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SPACEInterviewing LI Xiaodong, Professor of Tsinghua University
李晓东(北京) LI Xiaodong(Beijing)
56 图解 INFOGRAPHICS
从知识精英到知识无赖
Intellectuals Facebook: From Elite to Rascal
南蔻[城市中国]+张宜轩[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Fillipa(Urban China)+ZHANG Yixuan [UCRC]
58 老栗、老冯和土木宋庄
Li and Feng in Massive construction of Song Zhuang
栗宪庭(北京) + 冯峰(北京) LI Xianting(Beijing) + Fengfeng(Beijing)
64 在1960年代之后,继续做梦
访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文学院教授康纳利
Resume the Old Dream of 1960sInterview with Christopher Connery, Professor of Humanity Divis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康纳利(上海) Christopher Connery(Shanghai)
68 面向未来、踏实续脉
访《汉声》编辑翟明磊
Culture Production Toward FutureInterview with ZHAI Minglei, editor of Echo Magazine
翟明磊(上海+北京) ZHAI Minglei(Shanghai+Beijing)
72 给青年以梦,给城乡以希望
访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副院长娄永琪教授
Urban-rural exchange gives young people new dreams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OU Yongqi, vice president of College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 Tongji University
娄永琪(上海) LOU Yongqi(Shanghai)
76 “文化转向”:国家视角中的文化产业勃兴
“Cultural Turn”: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State Perspective
金元浦(北京) JIN Yuanpu(Beijing)
80 “中产阶级”的梦想及其终结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张闳(上海) ZHANG Hong(Shanghai)
86 中国海归的光荣与梦想
The Glory and Dream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田方萌 (上海) TIAN Fangmeng(Shanghai)
94 未来生活进行时 In City
走向新型城镇化 Stepping into a New Urbanization Mode
刘朝晖(上海) + 杨秀(上海) + 庞溟(广州) LIU Zhaohui(Shanghai) + YANG Xiu(Shanghai) + PANG Ming(GUANG Zhou)
106 逛街学 Street Roaming
对眼:孟买与上海之间
Gazing between Mumbai and Shanghai
袁菁[城市中国] + 黄正骊[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YUAN Jing[Urban China]+HUANG Zhengli[URUC] + Deepshikha Jaiswal(Mumbai) + Deepshikha Jaiswal (Mumbai) + Vikas Dilawari (Mumbai) + Ginella George(Mumbai)
114 想想城市 City Thinker
《落脚城市》:跨越疆域的旁观
Arrival City: A Boundaryless Observation
道格·桑德斯(多伦多) Doug Saunders(Toronto)
120城市热点 City Hotspot
124 英文黄页 English Version (Part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