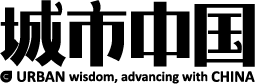文/冯原(广州)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祠堂竞赛所遗留下来的标本,已经变成现代社会极为宝贵的建筑遗产。当权力和利益的角逐纷纷退场之后,没有人会在意它们的原初功能,从过去社会中族群重新划分、争夺权力和利益的筹码转变成怀旧的乡土建筑的典范,祠堂的历史真相怕也要如过眼烟云一般消失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中了。
虽然生命的生死是个最古老、也是最“客观”的事实,但是生物学意义的死亡定义则是很晚近才出现的观念,追溯到久远的文明之初,如何体认和祭祀死亡可能是最具有多样性的文化观念之一。对于生者而言,祭祀再造了死亡的社会性,正是从社会整合的意义来看,死亡必须被仪礼化和空间化。《礼记》有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由此可以得知,借助祭祀的仪式能够建构出等级分明的社会。除宗庙之外,处置死者的场所还有坟墓,两者都源自于久远的祖先崇拜观念。事实上,宗庙和坟墓的出现与演进使得中国人在处理死亡问题上的方式迥异于世界上其它地域的种族文化,其物质和精神形式也构成了中华文化中的基底部分。
如果说宗庙祭祀是建立权力正统性的来源,并为帝王所垄断,那么从墓葬的经验中衍生出来的堪舆术适时填补了万民的生死观,并把单向的死亡再造成某种在代际间传递的能量循环圈,把逝去的个体重新拉回到生者的社会世界里。堪舆术有三个要素:分别是死者的肉身、自然之气和死者后代的福利。这样,在它的解释系统中,丧葬的主要学问在于如何在山川地理中发现藏风聚气之处,这些地方被拟人化地想象成穴位——深藏在地下的自然经络的“点”,由于优良的“点”总是稀缺的,所以,堪舆术指导下的丧葬便成为一种投资,把死者的肉身准确地葬入某个穴位,便取得了穴位中蕴藏的自然之气的代理权,最后,投资总是要追求回报的,由死者占有的“气”最终会返回或作用到拥有死者直系血脉的子孙身上,从葬入穴位到“气”的返回,达成了一个阴阳两界的能量循环。撇开“气”这个神秘主义的核心概念不谈,堪舆术的解释体系仍然有一个显见的弱点,与命相学宣称“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观念形成互补,堪舆术宣称的穴位天然存在于自然界,无论命的贵贱谁都可以去占有穴位,也正因为如此,发现穴位的“素质”与穴位的争夺战实质上必定会变成由堪舆术引导下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斗争。
与坟墓这种祖先的肉身居所相比,祖先的灵牌居所——祠堂——更值得我们去探讨它的意义。而祠堂之繁盛,以广东为最。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的“祖祠”一条里说:“岭南之著姓右族,于广州为盛。广之世,于乡为盛。其土沃而人繁,或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自唐宋以来,蝉连而居,安其土,乐其谣俗,鲜有迁徙他邦者。其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其曰大宗祠者,始祖之庙也。”这一段被广泛引用的短文揭示了不少有意义的信息。并间接指出制约宗祠建设的社会条件。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地肥沃,生齿日繁,更因为优越的地理条件强化了安土重迁的心理。从聚落的形态上,珠三角的村落基本上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传统。因此,以姓氏聚居的乡村即具有血缘上的认同,也具有空间上的边界,这个空间的焦点便是村里的祠堂。透过屈大均的观察,珠三角一带的祠堂数量是如此的密集,似乎超出了祖先崇拜的“正常”的需要,由此我们应该想一想,宗族无论大小都在祠堂上花费巨资、大兴土木,其结果无异于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祠堂竞赛。那么,我们自然有理由往下追问:明清时期发生在广东的这场祠堂竞赛,其用意何在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在坟墓与祠堂之间作一个简单的比较,与墓葬所制造的能量循环圈相比,祠堂起码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祠堂要比墓葬风水具有更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受堪舆术指导的墓葬追逐的是自然界稀缺的穴位,这个密码只掌握在风水师的手中,堪舆术安排的祖先坟墓虽然有着穴位选择上的机遇,但由于血缘上的排他性,再好的穴位也只惠顾以家为单位的直系子孙,这种“祖先期货”的投资即使很成功也并不能增进以宗族为单位的家族联合,这也就间接导致了社会整合的不足。当某些区域发生了更为剧烈的社会竞争时,以姓氏为单位的宗族比起以直系子孙为单位的家族而言,无疑会产生更大的规模和效益。如果相关的条件能够集中出现,正如在明清两朝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联合体的建构、维系和扩大就会成为极为现实的需要。只有获得了政治经济的支撑点,相关的象征空间才会被建构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祠堂是由宗族扩张的内在诉求形塑出来的空间形式和表征体系。
与堪舆术控制的坟墓相比,祠堂的另一项功能是祖先整合的灵活性。在穴位-肉身不能被虚构的前提下,祠堂祭祀则以祖先牌位的形式取代了祖先肉身;以更为显炫的建筑样式取代了神秘的“龙穴”,这种精神与形式的象征性更类似近现代用于整合民族国家精神的纪念堂。为什么是祠堂、而不是坟墓能够演化为宗族社会的核心?很显然,牌位祖先要比肉身祖先更能适时地应合需要。这种情况构成了祠堂竞赛的一个起点。当祖先并不取决于肉身,而是取决于修族谱造祠堂的行为时,通过对祠堂的扩大或是虚构祖先,祠堂祭祀能够整合更大的族群力量,并使得宗族权力制度化;此外,作为权力表征的祠堂与公田、族田等经济产业形成某种政治—经济的联合体,在后世更是演化成书院等,这种由象征空间转化出来的政治经济利益,实际上为族群角逐财富和功名提供了现实支持。
在前述的条件下,祠堂竞赛的结果自然是祠堂越多,其宗族越大,由宗族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利益也相应增加。清代以来,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豪门大族多数都拥有数量庞大的祠堂,以番禺的沙湾为例子来看,五大姓氏共建有100多座宗族祠堂。而最为显赫的何氏家族,就拥有祠堂87座。“沙湾何”当然也是珠三角(包括省港澳)一地声名显赫的旺族。透过这个现象,我们便可发现一个相互对应的多重结构:在客观的一面,强势的家族控制着最大规模的田产和收益;在象征的一面,大家族利用财力大兴土木建造宗祠。祠堂显然是物质财富堆砌出来的符号工具,同时又反身成为维护社会统治的象征力量。当“祖先的力量”成为弥漫于整个乡村社会的意识形态时,它一方面控制着弱小“杂姓”和“蛋民”们的屈从意识,又依靠客观性统治来限制他们兴建宗祠的权力。事实上的确如此,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居民既无本姓氏的祠堂,又无权参与祭祀活动。
祠堂竞赛所折射出的是珠三角特有的乡村统治模式:宗族想象维护着客观层面的现实利害关系。把岭南乡村中的等级秩序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以宗族区隔为中心的阶级对立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祠堂便是显炫宗族力量的空间符号。这样,在祠堂与宗族财力高度相关的前提下,兴建祠堂势必也会发展成一场谋求象征权力的争夺战。大量的金钱被投入到建筑行业,佛山石湾一带发达的陶瓷建材业多少都与岭南宗族社会的炫耀性竞赛有关。到了清代末期,延绵数百年的祠堂竞赛达到了顶峰,兴建于二十世纪初的广州陈氏家祠成为了广东祠堂的巅峰之作。广东全省陈姓共同集资的结果造成了这座集岭南装饰艺术之大成的建筑精品。然而,毕竟是由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控制着形而下的建筑工艺,陈家祠之所以被建造成一座象牙雕刻式的建筑,其根本的动因,还是因为精湛的工艺表征了所有者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展开这个道理,越是昂贵而华丽无比的宗祠应当越是会带来更多的现实收益;财富愈多就愈是需要兴建祠堂以增加象征权力。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一直延续到农业型社会瓦解的那个时刻,那也正是祠堂竞赛嘎然中止之时。
作为地下和地上的“祖先空间”,皇家宗庙、坟墓与祠堂建立了一个与生者世界完全对称的死后世界,并通过祭祀仪式把死者的力量反射到现实社会的斗争之中。在这个由祖先崇拜所操控的精神共同体中,死者从来没有真正的死去,借助于一系列精巧而肃穆的仪式,死者演变成生者扩张权益的玩偶。如果说坟墓界定了死者通往阴间的入口,也同时接通了庇护子孙的“气”;而祠堂却是社会权力的界碑,它的作用是借祖先之名来界定或扩张生者的权界,在祠堂的舞台上演的是象征与现实的双重游戏,进而去获取更大的真金白银的利益。与坟墓相比,祠堂更具有显炫的表象,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大的社会效用,因此,在某些社会条件集中出现的历史时期,如同在明清两代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社会中的祠堂竞赛很可能也会超过坟墓竞赛。在祖先的名义下,乡土社会中的祠堂成为一座座愈来愈华美的空间界碑。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祠堂竞赛所遗留下来的标本,已经变成现代社会极为宝贵的建筑遗产。当权力和利益的角逐纷纷退场之后,没有人会在意它们的原初功能,从过去社会中族群重新划分、争夺权力和利益的筹码转变成怀旧的乡土建筑的典范,祠堂的历史真相怕也要如过眼云烟一般消失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