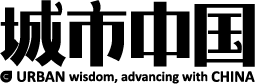本文选自《城市中国》第24期——深圳再生
文字:邹波
海口火车站比海口机场更远,可能是世界上离城市最远的火车站,在更深远的郊区,但一直沿着海岸线,火车站就是一个荒凉的海港,在它与城市之间,有一段良莠不齐的海滩,其中只有一小段开辟为旅游度假区,更像避难所,如果你谈恋爱的时候,跨出这个区域,就会有椰林中的“兽人”出现。我才醒悟,朋友提醒过的那段危险的海岸,是在城市与火车站之间,不是在万绿园文明的海岸。火车站与城市之间据说有一个长流镇,吸毒者来打劫的多,深夜有怪诞的歌声,在椰子林中。半吊子黎话。
在空空的候车室,警察查所有人的身份证,因沿海跋涉来这荒地的坏蛋,必于所有人之中抢劫所有人,厕所却是个大漏洞,小蛮仔长得跟赵传一样,有一个高大的新疆人走来走去,其实他很容易被人记住,但被查了好几回,深夜的海风寒冷,人们拥做一团,对面的候车室更空旷,轮船比火车的汽笛更频繁,有9个业余选手在排练健美操,大腿粗壮的西北女子,是什么系统又在海岛搞活动,后来没了踪影,我又敲打了一下空旷的B候车室,没有回音,那趟去西北的车,已经先过海了。A大厅里有一个旅行团在玩杀人游戏,都是一些老年人,迟迟不能进入状态,像每次会议的开端,有人闭着眼睛当平民,却就那么睡着了,没有来得及睁开眼睛指证,导游小姐主持了几回,累了,老头们的劲头却又刚刚上来,她在一旁看手机,像有心事,却有一个老头提着裤子从厕所出来:“靓女,你起来呀,我们继续玩。”羊脂球。
看到列车过海的注意事项,停电,没有光,没有广播,没有空调,阅读灯这支蜡烛可以开到微光,不能下车,什么都不能做,这还真让人有点紧张。果然是这样,铁路在船的甲板上,来回进退了两次,第一次没有成功登船,又退回到海边的荒野里,直到另一列去上海的火车停在我们右舷,它的硬座车厢里,似乎有一个光着上身的小胖囡囡在过道里吹海螺。看不清,听不见。船上的铁轨要和中国的铁路线吻合,所以会有班次几列不同的火车并排过海,却不能使同一列火车折叠起来,排成三列纵队。木甲板同岛屿隆隆地撕裂开。
看不见大海,舷窗遥远而黑暗,但看见车外水手和船舱的内部。没有颠簸,今夜连海床也非常稳定,列车员下车,点烟,和水手交谈,自己也变成了水手的姿势,叉着腰,卷着裤腿,潮湿的裤腿,我记得上火车的时候,车票在车外就提前换成了小牌牌,列车员说:“要过海了,要过海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忙。”但现在他悠闲得像个捕鲸者。大海的标志——一只小玛瑙一样的海苍蝇,飞进车厢。通体晶莹。
船上,火车的上铺,最闷热的窒息时刻开始了,我开始在想,我上一次这样窒息是什么时候,什么样子,更无形的上一次,象征的心情,多少年前,失恋、前途暗淡还是思维阻塞……这次是实在地发生了。猪笼。杀人游戏竟然又开始了,老人们却更加兴奋了,杀这个,杀那个,把铺位敲得咚咚响,磕瓜子,这个旅行团的铺位包围了我们,而那个女子就在我的下铺,疲倦的女导游更疲倦了,手机映出蓝色面孔,趁着老人们更加忘乎所以地玩耍,在黑暗中,她独自睡去。半个小时以后,又有人开始喊:“靓女,靓女,起来,起来……”她已不省人事。
过海的过程据说只有一个小时,我的印象却是一直到我睡着,这闷热和窒息、老人的聒噪,嗑瓜子的声音就是那样渐渐消失的,第二天醒来已是肇庆,广东的青山和香火,村落老远就能看见旗帜一样的宗庙,鱼塘和水田,塘底的矿,有人从水中捞煤,沥青中的水鬼,生锈的楼房,农妇半人在田里,戴眼镜的黑皮妇人,背上孩子从稻田中露出一个脑袋,“中国最好的季节啊,南国也是秋天……”,窗外的货车车皮上用粉笔写着端庄的楷书:“剑外忽传收蓟北……”,标语:“不准在铁路上行走,卧轨,喧哗”——针对诗人;标语:“火从心头起,灾靠小心防”——心之火。车厢尽头有广东话在交谈,男人接着开始念一个广告:“修身,致美,求……真”(“真”的发音如“增”,很庄重,如“锃锃”的钟的余音),一个黑龙江采购员有着丰富的历史政治知识,谈到清朝末年满人效法英国的贵族制度,改造自己的纨绔子弟,还谈到民进党的乡土政策和他们真正的人数,是壮大还是在萎缩……列车始终有许多货郎来回穿梭,包括过海时黑暗闷热的几个小时,他们打着手电,卖越南三宝,穿着铁路制服,这趟漫长的南北列车,似乎被一个伪善的生意人完全接管了。我讨厌一个列车员对着一个婴儿兜售彩珠笔的场面,刺花了她的眼睛。由此我觉得车上将没有人主持正义。一个小说构思的缺口。在过道里充电,继续读着《克里希那穆提自传》,他一生无所事事,只想和人性的弱点交谈,但有一天面临森林中的老虎,他也很镇定。我想起西川写过:面对高原神圣的黑暗与寂寥,那少年“放开胆子但屏住呼吸”。
我的中铺是一个中年人,从床上下来,整个人好像都浮肿了,昨天我看他孤独一人,穿着知青的衬衣,皱纹,清瘦而有神采,背着迷彩的双肩包,穿过检票口,现在是一个臃肿的人,是什么使他一夜之间变老了,他起来的第一件事是买了一大包瓜子。
“买瓜子,你是想报复使你失眠的人?”我冒失又过敏地问。
“ 使不得, 可不能这么说, 小兄弟, 阿弥陀佛。”一夜浮肿的中年人机警地双手合了一下什。窗外正经过了一条广东与湖南交界的绿色大河,松林边是芦苇,山有偶尔的丹霞地貌,云气低垂,也许是武水。韩愈流放时经过这里。我们开始大声地嗑起来。后来纵声大笑。他是个复员军人,现在却容易为脆弱的东西击倒,后来他重新是一个爽朗的中年人。大笑直到中午,中午的光阴是湖南的树影出现在那些老人的被子上,隐约的婴啼,是上午从肇庆上车的孩子,喂奶之后是静谧,每过一次隧道就更静谧。连续大量的隧道又形成了夜晚的常态。
嗑了一夜瓜子的老头老太们继续做着白日梦,鼾声穿过隧道的时候发出回声,有时他们的手自然地垂落在被子外,令你忍不住想去把一把脉,又是什么使他们昨夜如此亢奋,是过海这件事吗?年老而放肆的人,无论有什么罪错,为他们的生命力而高兴。导游小姐悠闲地在窗边看着《青年文摘》。Eco说:“人生充满了空闲。”到了晚上,他们的空闲——9点以后,过了汉口,在餐车里,吃了饭还不走的乘客被善意地劝走,本来一个人趴着喝酒的列车长也开始带着化装的货郎、警察、女招待、厨子,玩起了他们的杀人游戏,他年轻,肥胖,但是干部队伍中的精干者。我离开餐车时,突然觉得我也能驾御这国营的火车,穿过岛屿、海洋和陆地,可以轻易取代这醉酒的列车长,我什么身份也没有,我视我的国家为粗浅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