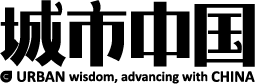【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式集体主义】
对中国而言,2008年可谓是其建国近60年以来最悲喜交加的一年。一方面,北京奥运标志着这个曾闭锁于世界的共产主义大国所努力实现的国际化转型;另一方面,雪灾、地震等接踵而至的特大天灾和发生在藏区的骚乱、以及随后奥运火炬在境外接力受阻等人祸,则令这一年的国际化之路格外坎坷;国际化令中国股市经历了亿万财富瞬间蒸发、无数股民集体幻灭的危机,也成就了中国首次作为奥运东道主的全球化身份和亿万国民的集体信心。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所制造的巨大张力,将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上记下最福祸相依的时刻。
中国的国际化是艰难的,不仅中国的计划体制与国际的自由市场在本位上存在着矛盾,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传统和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根基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更有着差异;计划体制与集体主义在现代共产主义运动中结合而成的“集体运动”,不仅为上个世纪的持续革命提供了浓墨重彩的底色,也为今天来到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提供了中国特色的语境。中国的国际化过程,势必是一个沟通与隔阂、理解与误解、作用与反作用共存的过程;而中国的现代化越不同于西方模式,就越有可能因遭受国际世界的误解而内聚出从国家到民众的集体主义能量。不理解这种能量的历史脉络,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治理之道和民众的集体心理;而对这种能量的把握不当,中国也难以真正融入国际社会。2008年不仅是中国的“世界年”和世界的“中国年”,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新解读“集体运动”的契机。
【集体与集权】
集体性描绘了千差万别的个体之间的共性,而集权则将这种共性转变成为移山填海的巨大能量。然而,历史上最早并不是因集权而产生了这种能量,而是因为需要这种能量而产生了集权。中国第一个以国家形态出现的集权王朝夏,正是产生于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巨大洪灾;而成功治理了这场灾难的大禹,则以“大难兴邦”的方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集权帝王。他在治水过程中不仅建立起了庞大的水利工程,更因为实施这种工程需要远远超越个人的力量,而设计出一种能够“举国之力”的集权组织——国家;他通过自己建立起的国家,将民众团结成在重大灾难前同舟共济的利益共同体,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如何将乌合之众组织成“有力、有序、有效”的团队的这一命题。
“治水”成为了“治国”,这显现了灾难和政治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与经济的发散性不同,政治更多体现为对外来灾难和内在危机的内聚性治理;而外来灾难和内在危机在民众集体性的塑造上往往也有着相反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正是在以高度军事化的国家组织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国状态后,迅速因为内在危机而土崩瓦解。
在应对强大的外来灾难时,集权国家往往能够通过共同利益的诉求,将代表不同血缘、行业、籍贯和族裔等的利益集团凝聚成一致对外的集体力量;而在这种外来威胁消失之后,这些群体之间在内部权利分配上的固有矛盾便重新浮现出来,集权模式就会被指责为“通往奴役之路”。集权国家在动员资源和平衡利益上的矛盾,不仅成为秦王朝昙花一现的深层原因,也成为此后的大一统中国在其两千多年的集权传统中的长期难题。
秦朝之后的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呈现出分裂和大一统交错前行的轨迹。相对于国内的分裂和地方势力间的战乱,实现政治、经济、交通、文化、语言、文字和各种标准上的大一统,则被视为维持社会稳定、消减内耗的一劳永逸之道。中国地域的广袤和地方社会的多样,使大陆国家的中央集权模式较周边国家更为庞大、昂贵和复杂,也使得中国的集体主义有别于韩国刚烈的半岛性格和日本孤傲的岛屿性格,显现出更多作为大陆国家的包容性和文化中心的正统性。中国集权的高度和集体的广度,一方面生成了庞大的官僚集团及其伴生的人治与腐败,另一方面也在营国造城上产生了大量举世称奇的纪念碑工程,同时在其文化的生产和输出上成为亚洲集体主义的中心。集权体制在治理上的专制和在文明上的高产,成为今天西方对中国崛起敬畏交织矛盾心态的根源。
【族裔与阶级】
秦始皇以法家所推行的国家集体主义,为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体系化的基础;然而,由于这种准军事化专制在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上过于刚性,以“废分封、立郡县”的中央集权取代了诸侯林立的地方自治,地方势力的反叛使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此后的王朝则将高度垄断于中央的权利分层次、有限度地向民间下放,形成“国”与“家”、中央政府与地方宗族、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集体主义从而向国家与地方两极演化:前者强调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整体利益,因而逐渐设计出文官充政、人事回避、家族连坐和保甲编组等旨在弱化和控制地方势力的制度;后者则强调在国家给予的县政以下的自治空间中,以地方族裔集体主义为中心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外儒内法”的治理结构,逐渐成为此后千年中努力维持大一统格局的集权中国的主旋律。
作为前现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族裔集体主义是农耕文明的必然产物。以土地为中心的农耕文明强调对土地超越世代的驻守权,个体只有在祖业家产和亲缘纽带的集体主义土壤中才能获得穿朝越代的能量;而作为代价的是:个体的选择也必须符合整个族群的整体利益才能获得作为族群成员的合法性。这种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献精神,至今依然是中国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农耕文明对于中国式集体主义最大的影响,在于其将土地生产与人口生产相挂钩的模式;“多子多福”被视为一种家族的投资,将现世的有限资源用于无限的未来。在未来中延展的子嗣谱系要么成为土地上的劳动力,要么成为家族财富和宗法门庭的管理者,以及作为族群的触角向国家和社会系统渗透,从而成为隐蔽的族裔集体网络的有机节点。这种建立在“无限资源”前提上的人口模式,尽管周期性地经历着人口红利耗尽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却在总体上以“人海战术”,对外来文化的稀释和少数族裔的同化上起到了以柔克刚的作用。正是这种建立在巨大人口基数上的集体主义,使得中国作为一个古文明体能够不间断地延绵至今;而“人海”集体主义的大规模和不可战胜,也在日后造就了西方的“黄祸”恐惧和“中国威胁论”。
源自宗法社会的族裔集体主义随着生产方式的升级而转型,从适应农业生产的家族集体主义到适应商业贸易的乡族集体主义,再到适应工业生产的阶级集体主义;近代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边缘化激发了民族集体主义;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则将之组织成为国家集体主义……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集体主义的一个转折点,新政权不仅完成了国家集体主义和阶级集体主义的高度复合,而且以“第三世界”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的外交战略,将阶级集体主义国际化。无产阶级摧毁了过去垂直一体化的地方宗法势力,但沿袭了其集体主义价值观,即个人在集体中的无条件服从。自我牺牲精神感召下的海量群众与国家动员相结合,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演变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种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和明确运动目标之上的集体主义,将个人微缩成集体中的平均微粒,个人回忆变成了有关集体移民、集体学习、集体宿舍和集体劳作的集体回忆,个人生活成为了在群众运动中随波逐流的集体生活。然而,一旦这种集体主义失去了其运动目标,其利他主义基础也将随之丧失,个人主义将在信仰的集体失落中叛逆性地反弹。
【国家与社会】
上层建筑在基层的无为和以士绅为基础的地方自治,是族裔集体主义的制度成因;而中央政府也通过“藏富于民”的放权让利维持地方自治的稳定;科举制则在地方社会与上层建筑之间设置通道,其中选和落选的人才分别成为了政府官员和地方士绅,事实上也分别成为了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二者在前现代中国的双重繁荣,使得国家一方面可以维持宏观结构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又不失民间微观生态的丰富性。
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共生关系在曲折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被改变。苏式的国家集体主义与中国工农运动结合而成的战时集体主义,成功地将基层社会动员成与旧秩序分庭抗礼的颠覆力量;而“社会主义”的理念则重新了定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然而,对于长期在战争环境中形成的国家集体主义,尽管它在大规模资源调动和凝聚民心方面极具优势,但在如何将战时的斗争哲学转变为战后的治国之道方面,却缺乏足够的成功参照。战时的动员经验被沿袭到战后,上层建筑藉由无微不至的党团力量和基层组织向社会渗透,集体运动中的社会力量不得不听命于国家动员,同时在建立社会规范和自我完善方面逐渐失去其应有机能。在一个缺乏社会规范的环境中,国家不得不通过树立各种英雄和榜样强化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社会道德与职业规范。正如阶级斗争需要通过树立假想敌来获得动力,集体运动需要树立明确目标、而不是通过严密公正的法规和潜移默化的道德力量,来驱动社会细胞在一定规范上运行。国家集体主义造就了无限责任的全能政府,而社会力量在国家事务中的长期缺场则导致了社会机能的萎缩;这不仅使那些本可由社会自行消化的事务成为了责任的真空,而且也存在将集体主义推向“暴君-暴民”非理性极端的危险。今天,即使在文攻武斗的文革时代过去多年之后,这种集体非理性依然大量地以语言暴力的形态出现在网络空间;网络社会的野蛮化和部落化,事实上正是物理社会在个人膨胀、常识丧失之后走向“自由而封闭”的缩影。当年在国家集体主义中被压缩的公民社会空间,将成为今后“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不得不长期弥补和培育的对象。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改变了集体主义在中国的形态。“改革”在内容上将集体的话语权向社会下放,“开放”则在语境上将这个集体向全球推广。在上层建筑从集权向威权过渡的同时,刚性的国家集体主义则向外柔内刚的后集体主义转型。耐人寻味的是,上层建筑在群众运动方面的传统没有就此断裂,而是从单纯的政治运动转向更多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方面的诉求:从批判走资到打击腐败,从“学大寨”到“学小岗”,从灭“四害”到“创卫”,从学习时传祥式的自我奉献到学习“傻子”式的勤俭创业,从样板戏到模板化的春节联欢晚会…… 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同步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后集体主义”,显示了二者在中国的一脉相承之处。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令世界见证了中国在短期内应对突发事件而动员资源的规模和效率,同时也令世人在共和国建国近60年后重新理解国歌中“我们万众一心”的内涵。这场发生在奥运前夕的灾难,将一个集权国家的危机管理能力展现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这不仅给世界一个重新理解集体主义的切入点,也给了中国一个引导和培育自身社会力量的契机。对于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够有力、有序、有效地应对自然危机,而健全的社会则是消解潜在社会危机的长效机制。
【体育与运动】
以在现代世界复活,在于它基于人本的定位超越了性本位、神本位、权本位和资本位等人类关系,从而也超越了性别、信仰、等级、阶层等人际隔阂;而中国也相应以“同一个世界”的大同理想回应五环相连的奥林匹克精神,以“和谐世界”理念与共和国建国之初就铭刻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世界人民大团结”遥相呼应,从而造就了东西方两大古文明体在乌托邦理想上跨越时空的对话。
“体育”(Sport)与“运动”(Movement)在现代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因缘关系。“体育”通过挑战人类身体极限展现了“更高、更快、更强”的个体意志,而“运动”则通过大规模的动员与合作展现了“万众一心”的集体意志。当运动员背负着国旗出现在竞技场上时,个体与他所属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国民便成为了“名誉共同体”,个体在意志力上的“临界体验”将为他所代表的集体所共享,从而以一个国家英雄的身份起到带动集体意志、提高国民凝聚力的效应。因此,尽管极限运动在其超负荷方面常常有悖于体育“健全身心”的初衷,但由于它在强化意志方面对群众所起的动员作用,体育成为了集权国家在群众运动中的重要战略和集训体制下的政治任务。
而对奥林匹克而言,奥运的辩证法就在于结合了个人突破与广泛参与,一方面强调个人在公平竞争中取得意志的胜利,另一方面,它也通过鼓励更多全球范围的群众参与,将这种胜利超越于简单数据之上,在同一竞技台上实现不同国家、民族、种族、宗教的“平行世界”,而成为跨国界集体主义的胜利。从开幕式的宏大叙事到比赛中的动人细节,奥林匹克运动全面而深刻地展示了国际运动的乌托邦性质:大量竞赛被集中到同一时空,同一事件在全球媒体同步转播,各国国旗在场馆中同时飘扬,无数互不相识的观众集体喝彩…… 尽管这一海量化的庆典景观对于有着集体运动传统的中国而言并不陌生,但奥林匹克运动对于中国的意义,更多在于它展现了“和而不同”的全球大家庭景观,这对曾经过于求同的当代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借助于奥林匹克运动,中国获得的不只是破纪录的奖牌数字、大国崛起的象征意义或失而复得的民族自信心,而将更多是从国家到社会的转型动力;中国式集体主义也将因此在“天下一家”的理念下,以独立而开放的姿态融入到世界大集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