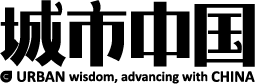文/张宜轩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边走边想象,边看边研究】
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研究城市的人通常身在城市;而且最好是游历四方城市,在所有的城市标本上添加个人注释。他们不像人类学家,所去到的地方最好是偏远的地界,研究的是鲜见的文化。他们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学家,绘制地图和编撰方志,以超越的眼光打量眼下的世界。他们更不可能去效仿康德,终生不离格尼斯堡半步,任思辨在时空中延展。
西方的人类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经历了从“我者”走向“他者”再回到自身的过程。而甫一开始,城市研究者都已在城市中生活很久了。所有想在城市里找到生活答案,或在生活里找到城市根本的努力都是完全的“参与式反思”——以一个肉身的存在于城市中经验城市,再对此经验进行反思。当恩格斯行走于伦敦的贫民区时,工人阶级的居住状况就在眼前,就在与自己同住一城的人身上发生着,他发出了同情的呼号:睁开眼睛,绕过城市干净整洁的街区表皮,看看背后的惨状吧。于是,改变城市居住状况的各种努力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而同时代的社会学家齐美尔以及他的学生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基于魏玛时期柏林的生活体验,在城市人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作用下,也急于剖析当时资本主义城市的社会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这种急切的心情让本被邀请开课演讲“知识分子对城市影响”的齐美尔,转而将课程内容改成《大城市与精神生活》。大城市的生活,特别是金钱对个体的“异化”已经渗透了个体精神、公共生活甚至是艺术领域:金钱观念“掏空”了充盈的人性个体,而橱窗美学打开了商品拜物教的大门;公共生活被内卷化,艺术家开始明码标价。在那个时代之前,这些都从未发生过。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们疾走于书斋课堂之间,城市社会的现实如风景般掠过眼帘。
20世纪之初,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俨然视城市为一个偌大的实验室。他们在芝加哥的红灯区、贫民窟中寻访,他们视自己为医学家,诊断城市的病症,而后又自视为科学家,欲总结出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铁律。在详尽有序的调研记录之间,波德莱尔曾在巴黎街头所捕获的《穷人的目光》已然脱去了故事的细节,不同阶层在城市空间上的分隔已经成为更坚固的现实沉淀。
在场的斗争,不在场的反思时隔半个世纪,记者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批判美国城市街道生活的索然无味和规划失当;城市失去了活力,规划师还在“为谁规划”。雅各布斯大作落笔不久,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在巴黎街头带领学生运动,同时也以著作阐释资本主义世界中“空间生产”的涵义。同期,地理学者大卫·哈维转从英国西岸的布里斯托尔转往大西洋彼岸的巴尔的摩任教。发达资本主义的轮盘已经转到第二次经济危机后的去工业化时期。此时,巴尔的摩的滨河区改造启发哈维读懂景观变迁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制。他组织学生研读《资本论》,从中读出了一层“空间”的新意。
知识分子集体发声:这是“谁的城市”。冷眼旁观和参与观察的调研在多维交杂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矛盾下已经不能满足解读城市的需求。与其同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对城市进行“结构化解读”:它超越了对城市中活动与地点的互动机制描述,从而去发现空间形式的生产和功能的结构性规律。研究者的眼光往往追求“穿透”现象之感,然而,一个好的研究者必须是在场的目睹者;生活在城市是研究者在场的最好证明。
在他们眼中,城市的一部分死了,另一部分活了;一个城市衰落了伴随着另一个城市的崛起。曾经,那些怀着乌托邦梦想的城市实践家和城市评论家的口中不断出现的提问——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吗?已经越来越多的被更为具象的问题代替——这个城市会好吗?在全球化的当下,当时空压缩前所未有的将城市观察家和研究者本身稳妥的镶嵌在高速运转的学术生产机制中,裹挟着他们前进时,城市生活的潜在优越性常被暗藏不表。
【巴黎——在文字里想象的现代性之都】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巴黎,可说是十九世纪城市体验的先锋地带。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通过解读抒情诗人波德莱尔的诗歌意象透视当时的社会和人的状况,并将浓缩于十九世纪巴黎的造物和景观之中的现代性一一释放出来。时隔半个世纪,大卫·哈维在其《巴黎,现代性之都》中,以历史地理学者的结构化眼光,将本雅明式的分析带入一个更宏伟的框架中——一个物质化的巴黎在空间、金钱、土地、劳动力、家庭、消费、景观、造城等主题中。当本雅明与波德莱尔相遇时候,当大卫·哈维与巴尔扎克又在巴黎相遇,而他们的城市想象力则在由诗歌、物品的发明、小说、统计数据、史料记载所编制的网络中生发扩散。如果说这些碎片化或者结构化的想象力有什么中心的话,那么现代性的意蕴则是一根隐形的轴线;它与理解一座伟大的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文字中我们想象巴黎,想象现代性。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归纳过程,而是一个历史地理特殊性的时代精神表征。
【洛杉矶——机械复制艺术时代的城市】
巴黎的现代性之维虽纷繁,但至少还可从文本与西洋景中窥到一丝真像的影子;二战前后的洛杉矶经历了美国的新政、战争时期和麦卡锡时代;在此期间,现代性的对立紧张关系仿佛都被一批批南来北往的移民和消费式艺术创造消解了。此时的洛杉矶,好莱坞电影大行其道,美国中产阶级日渐兴起,一切过于美好的政治愿景社会蓝图都会在这里最终归宿。在战火中逃离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的加州似乎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城市评论家迈克·戴维斯在《石英城市》中如此说道:“相比于美国其他地方,洛杉矶就像一处准乌托邦,而相比于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整个美国也像一处准乌托邦一样……对于南加州诞生过程中那种奇特的历史逻辑,他们或是懵然不知,或是漠不关心,听凭自己的第一眼印象自动变成了神话:洛杉矶是个庸医窥测资本主义前途的水晶球。”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带着“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人马顺次来到此地,并很快在地广人稀的南加州遭到怀乡愁绪的困扰。“除了极少数例外,人人都苦闷地抱怨着见不到欧洲式的civitas(城市)——甚至连曼哈顿式的城市景象也没有——见不到城市里的公共空间、成分混杂的人群、历史气氛、抱持批评立场的知识分子。”
所幸,处于法兰克福学派边缘的本雅明一直游走于欧洲大陆,间或致力于完成他的“拱廊计划”。他并不情愿离开,而最终当形势迫人时,却被“自由世界”拒之门外。不愿落于纳粹之手的书生最后走向了自杀的归途。讽刺的是,本雅明所洞见的艺术作品的“光韵消逝”却在他没能去成的洛杉矶影射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化工业运动,即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发展。加州城市的想象与现实彼此互为复制物——声称为艺术的电影在光影重叠的胶片上复制了“光韵”,也记录它的消逝过程。
根据本雅明的定义,艺术作品的光韵就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城市一如这“贴近之物”,在我们的眼底做“独一无二”的呈现,但它如此丰富广大,以至于我们不停的问,在怎样的距离去把握何物。而在135mm的胶片纸上,所有的时空景象都被限定,观影之间,我们将关于城市的想象力投射在这个有限的框架里。当电影结束,一切都消逝了,城市只不过是万家灯火之中一间被高科技音像设备所包裹的黑漆漆的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