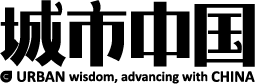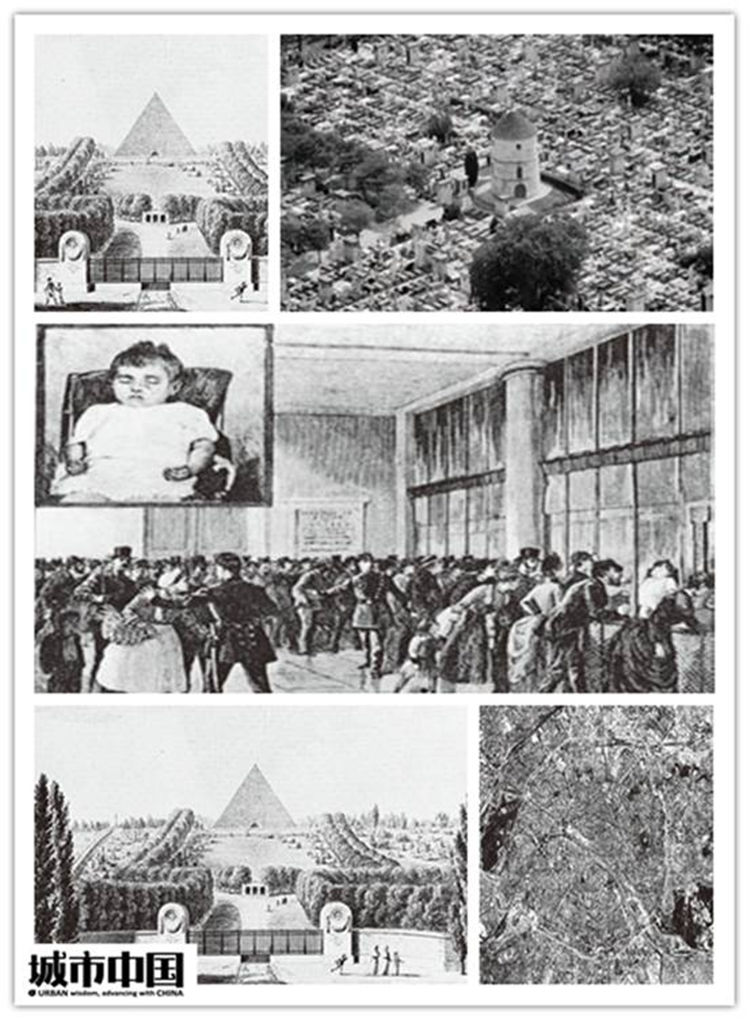文+编辑/唐凌洁
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奥斯曼规划中,位于巴黎北郊的梅里奥塞公墓计划几乎无人提及。在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我们不难发现,公墓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黎的都市机理重建后,它的墓地也呈现出理性的现代特征:以网格状排列的墓碑显得整洁、有序,与先前杂草丛生的墓地大相径庭。前者好似奥斯曼改革后的现代巴黎,而后者则呼应了中世纪时期那个瘟疫与游击战肆虐的巴黎。作为死者的世界,公墓如同镜子,映射出鲜活世界中的规则与矛盾。
镜像内外的巴黎Centre and Periphery as Mirror Images 1850年至1885年,巴黎城好似一位被硬生生撩开黑纱、套上现代洋装的中世纪妇人。林荫大道打穿了昔日密集的工人阶级区,将古老的市区拦腰切开。膨胀的房地产市场与气派的百货公司,精确地分隔开居住、休闲与工作空间,塑造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想象。
这是一个缓慢而野心勃勃的重建过程。改头换面后的现代巴黎,是欧洲有闲精英们消遣娱乐的天堂。那里终日充斥着成批到来的游客,幻想在景点的导览词中体验巴黎的过往。然而关于巴黎的真相并不在此,在数公里开外的市郊,还存在着另一个巴黎。那里容纳了城市的大部分人口,也与此同时容纳了愈演愈烈的社群冲突。对比那个精致华丽的时尚之都,被放逐的巴黎市郊好似另一个世界。
市区与市郊,构成了镜像的两端。如同照镜子时,镜子里的梦幻自我虽说在镜面上占据一个真实的场所,并重构了站在镜外的真实自我,却并不真实存在。因而,反映在镜子里的二维影像是一个不真实的在场,一个没有真实位置的乌托邦,一个“不存在于任何地方的地方(a placeless place)”。这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给异质空间下的定义,在1967年完成的《论异度空间》中,他这样写道:“镜子使我此刻身处的这个地方绝对的真实,与周围的所有空间联系起来;镜子也使得它绝对的不真实,因为只有当穿过了远在那儿的那个虚拟点之后,它方能被感知。”
福柯以公墓为例,阐释了这段话的意义。他认为,公墓的存在既是现实需求的反映,又与之彼此矛盾,挑战着它的合法性。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公墓不仅完成了从教堂坟场到公共空间的世俗化转换,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场域。因为安息在公墓中的人,曾经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地区,有着迥异的民族、语言或信仰,组成了一个异域的集合。
细细想来,巴黎市郊与巴黎公墓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它们的规划、选址、历史和变迁,都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雷兹(Philippe Ariès)曾在《西方的死亡态度》一书中论述道,欧洲人对于生和死的区别对待开始于18世纪末,其代表是1780年圣婴公墓的关闭及清空。墓中的骸骨被转移到了蒙巴纳斯街区的伊索尔墓园,而圣婴公墓原本位于巴黎城中的雷阿尔区。事实上,在随后的一百年间,巴黎公墓开始不断向城市边缘外移。
与公墓的运动有着相似轨迹的,是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社区。巴黎重建伴随着区一轮又一轮的绅士化运动;在被推倒的贫民窟原址,大量新潮的米灰色“奥斯曼式住宅”替代了原先阴暗、狭窄的传统街区。它的一层为商用门面房,顶层建有帽状佣人间,很快,这种为贵族定做的六层楼建筑开始风靡欧洲。同时,大批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小业主被迁至尚无基础设施和卫生系统的郊区。波布区和玛黑区南部是仅有的未被拆除的巴黎老区,原本拥挤的贫民窟因更多人口的搬入,而成为当时的“重灾区”。与公墓一样,阶级的空间隔离与边缘化属性在城市版图上变得一目了然。
公墓和城市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死亡,与诸如贫穷、传染病、酗酒等社会问题一同,被视作“不雅之物”,让讲究洁净、得体的中产阶级避之不及。作为死者的世界,公墓如同镜子般映射出鲜活世界的规则与矛盾。
城市理论中的公墓Cemetery Space in Urban Theories直到18世纪末,巴黎公墓大多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紧挨教堂而建,并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藏骸所内,不难见到数具尸体堆放在一起的情形,以至于有时,连死者的身份都难以辨认;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立有墓碑或雕像,占据一个独立空间的个人墓穴。
在一些天主教堂的内部也设有坟墓。这种将神圣的教堂和低贱的尸体混放在一起的做法,只可能发生在18世纪。受启蒙思想的感染,当时的文化趋向“无神论”,人们对灵魂与肉体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剧烈转变。在中世纪,人们普遍相信灵魂不朽。然而当这一观念在启蒙运动中被逐渐摈弃后,灵魂的存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身体反倒“复活”过来,成为膜拜的对象。在“无神”社会中,尸体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因为它是我们还存在的唯一痕迹。也正是在此之后,巴黎民众对墓地的需求大幅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墓从城市中央到外围的迁移。
建筑学者米歇尔·韦尔纳(Michel Vernes)清晰地勾勒出了社会阶层与公墓外迁的关系。他认为十九世纪早期的欧洲城市,包括街道在内的开放空间承载着容纳穷人的功能,供他们从事生活、生产、交易等主要日常事务。富人们则大多在自己的府邸中闭门不出,高高的围墙为他们提供了庇护。因而,当时的街道形态大多如迷宫般错综复杂,这样的设计,旨在方便熟悉地形的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在小巷中自由穿梭,以最短距离到达目的地,搜寻维持生计所需的基本物资。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穷人无异于危险的暴民,室内空间则确保了他们的人身安全。
但是1832年爆发的流行性霍乱令他们意识到,穷人的危险性不仅于此。疾病首先从卫生条件简陋的贫民窟开始蔓延,在城市的肌理上留下了令人胆战心惊的伤疤。城中那些不知通往何处的台阶,等候在下一个街角的未知威胁,古怪而扭曲的街道,映射出霍乱幸存者因病损毁的容貌,这令当权者恐惧万分。因而,在奥斯曼重建巴黎之前,当局已然开始尝试将“死亡”的印记从城中抹去。秩序井然的巴黎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将污浊之物扔到城墙之外,包括在城郊选址兴建公墓,避免生死混居,以及将公共行刑场迁移出市区。
但是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公墓承载着重要的文化和道德传承意义。它必须徘徊在日常生活周围,却不能靠得太近。亨利·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中论述道,对于那些巴黎的原居民来说,墓地不仅意味着一个存储遗骸的地方,它们提供了一个与上帝或先辈直接对话的媒介:“它将城市与隐蔽的、神秘的、地表之下的空间联系起来。……生者与死者的纽带,如同生者之间的纽带。”列菲弗尔将墓地归类为“绝对空间”而非“抽象空间”。正是这一属性,赋予墓地在一个社会中重要的文化价值。它是一个强有力的符号,向大众传递着道德准则。
奥斯曼化与墓地之争The Paris Cemeteries Haussmannized and the Resistance奥斯曼重建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位于巴黎北郊的梅里奥塞地区兴建大量公墓,并用精密的铁路网将其与市区相接。虽然公墓外迁在法国大革命后便已开始,然而在巴黎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向外辐射的市区面积将它们–拉雪茲神父公墓、蒙马特公墓和蒙帕纳斯公墓–重新纳入到了城市边界之内。
1881年11月至1882年1月间,梅里奥塞公墓方案一经宣布,便招致了大量反抗集会、海报和请愿书,迫使最终,这项耗资巨大的征地计划在一片反对声中搁浅。据当时的警方记录显示,反对集会的主要地点是“饮酒场所”,参加者则大多被指认为是“工人阶级”。他们反对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公墓的地理位置过于遥远,二是鉴于从过去三十年的公墓拆迁中,土地投机商赚得了巨大利润,市民对利益的分配缺乏信任。但是在这些反对意见中,警方报告最终概括出了一个共同主题:一旦梅里奥塞公墓方案被当局采纳,“全巴黎的大门将对工人阶级关闭。”
另一批反对之声来自毗邻规划中的公墓和铁路线的弗朗孔维尔。小镇镇长亲自起草了请愿书,由居民签名,阐述了“死者崇拜(cult of the dead)”对一座城市历史和工人阶层的重要性。同时,镇长本人也表明了自己对公墓方案的立场:大量不受欢迎的穷人将随着公墓搬迁于此,这会打破小镇上流社会居民的宁静生活。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很难将公墓片面地理解为现代都市的基础设施;正如列菲弗尔所言,在个人层面,公墓同样扮演着重要的文化角色,它将个人对集体的身份认同,个人对社群中其他成员的归属感具体化。在旧巴黎,公墓的诞生意味着“死亡”与宗教事务的分离,是灵魂重生的对立面。在现代巴黎,它成为一个意义和力量角逐的场域,是看似秩序井然的城市本身的对立面。与此同时,崭新的巴黎正通过重塑城市空间书写大众记忆,将那些“低贱”、“边缘”的部分抹去。
化作都市奇观的死亡 Death as Urban Spectacle 1895年4月3日,位于塞纳河右岸的巴黎太平间前人头攒动。这是一座建于1864的古典主_义建筑,高耸的石柱顶端刻有法兰西共和国的格言:“自由、平等、博爱”。两天前,巴黎警方在塞纳河叙雷斯城段(坐落在瓦勒里昂山,俯瞰巴黎及其区域)接连打捞起两具无名女童尸体。她们的遗骸被运往太平间,摆放在陈列室中一块巨大通透的玻璃橱窗后。
陈列厅的设立,原本旨在帮助警方早日辨认死者身份,却被Thomas Cook公司的权威旅游指南列为巴黎“最不可错过的景点之一”。一周七日,从黎明至黄昏,各式各样的巴黎市民和欧洲游客如潮水般涌向太平间陈列室,迫使巴黎警察厅不得不加大警力,在太平间周围拉起供游人排队参观的护栏。
是什么令世纪之交的欧洲人如此着迷?首先,无名尸体的耸人听闻效应,在于它完美释义了大都会文化的匿名性。在熟人构成的乡村社会中,横尸街头却无人认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太平间陈列室的玻璃不仅有效阻隔了生者与死者的世界,人们还得以透过它那透明的表面,凝视原本归属神秘主义范畴的“死亡”,并将其化作景观社会的一部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死亡正越来越多地从巴黎人的日常体验中脱离出来。对于那些掩面惊呼的来访者来说,陈列室中的尸体,无异于畸形秀中的侏儒。它们真实存在,却又陌生怪诞。
有趣的是,在世纪之交的欧洲,当公墓从城市版图上被抹去后,城市本身却成为了一个收藏“残骸”的巨大坟墓。“在任何一个现代城市,你几乎能找到任何类型的博物馆。鲜活的现存空间与死亡的考古空间之间的界线将慢慢消逝。”在走访了法国荣军院博物馆后,法国哲学家、城市理论家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给出了这样的评述。如果说,公墓是一个供生者祭祀死者的城市,那么旅游业主导下的当代西方城市,则可以被视作为一个供游客祭祀古老的碎片和已经死去的过往残骸的文化坟墓。
讽刺的是,劈开公墓的所有文化或哲学隐喻,是视觉/美学价值为其赢得了1 9 0 0年巴黎世博会的“优秀勋章(M e d a l o f Excellence)”。在世纪之交的大都会,一切鲜活之物都可以被摆入橱窗,成为令人眼花缭乱、微微颤栗的观赏品,连死亡也无法赦免。被视觉化和奇观化后的死亡,从旧时人们对腐烂的尸体和传染病的想像中跳脱出来。沿城市边缘而建的公墓,网格状分布的墓碑,都暗喻着规划、秩序和理性,好似一幅平和、寂静的风景画,用抽象的死亡掩盖所有的不堪、疼痛和恐惧。